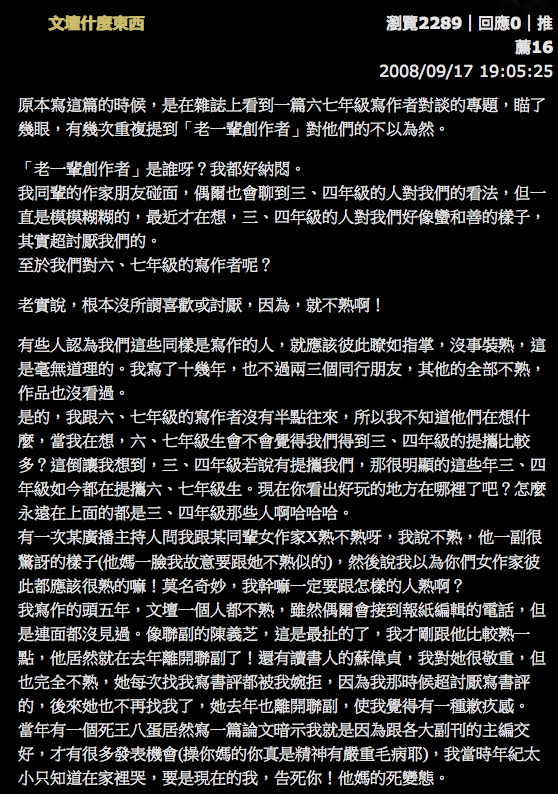
(笑紅那天寄來這位小姐的文章,隔天我立刻在聯合報那兒拜讀這位小姐的這篇作品。感覺「文章」這種產品,好像爛掉了一樣。)
我真的不喜歡這位女性作家。何必將語言表現地如此暴力(講好聽是隨性)。
每個人都年輕過、荒唐過,或者(企圖)以一種玩世不恭的心態來抵制、抵抗、反對刻板制度下的一切規則,並且從這樣「精神對抗」過程中,得到自身存在的快感和回饋。
是的,這種「對抗某種程度的體制」心態可以得到某種尊敬(至少對自己),也具備某種潦倒的浪漫。這一切都不難理解。但是,那又怎樣?
至於那句「我寫作的頭五年,文壇一個人都不熟」,不曉得張大春您熟不熟?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