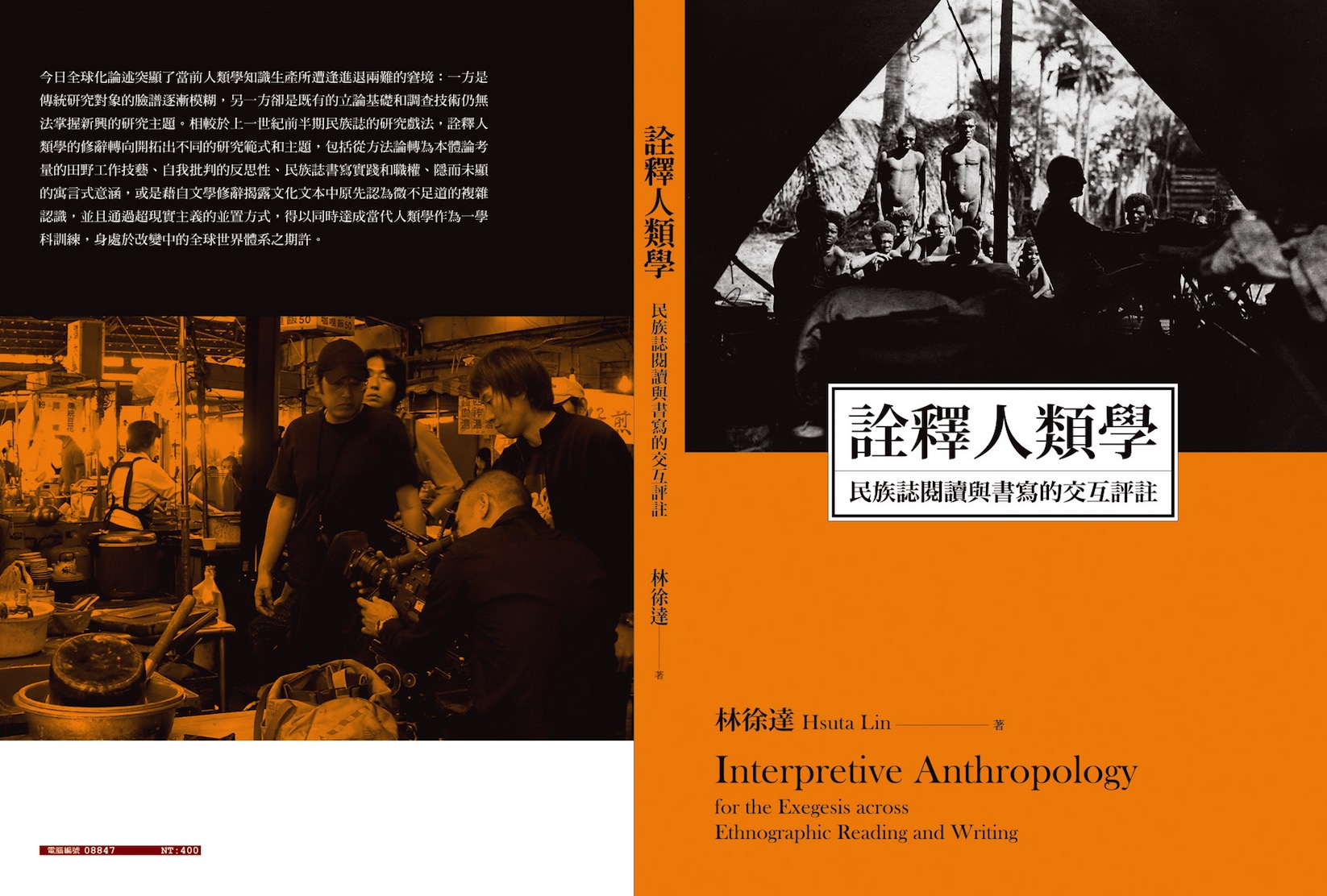
序 充其量,我們都只是聽故事的人
人們總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提領自身境遇,用這種方式讓旁人瞭解自己。但我們最終懂得瞭解是一種不斷的陷落,愈跌愈深終至成為一項折磨,因而給出關於人的荒謬性以及一股叫人無法自拔的墮落。於是自己努力於「毫無意義、毫無價值地活著」,在別人誤識的縫隙中得以稍稍喘息。
安德烈‧布賀東(André Breton)這麼說著:「我總得和自己辯論,才能解脫一種很溫柔、過分令人舒服地持續著而終究會將人粉碎了的擁抱。」那麼,如何和「幸福」相處?在這般無助的大環境底下,一方是沒有太多的希望或是奢求,另一方卻是無可救藥的理想夢囈。於是,我們偏愛一種折磨自己的行為藝術:將精神關到牢籠裡,或是把肉體丟進茅坑內。我們刻意用膚淺的存在主義實踐,作為一項直白的重鬱手段。以為透過如此痛苦,可以直接瞭解什麼是「生命」,所以我們也等待救贖,確信有一天有人將自己從屎糞之中拯救出來,並且沈迷於生命的價值、理想的堅持、同志的奮鬥、擁抱的承諾,或是永恆的愛情。彷彿自己始終夾擊在瓦特‧班雅明(Walter Benjamin)的「彌賽亞時間」:介乎虛無主義與人性、歷史與片刻、救贖與寓言性的當下。那是我們內心唯一的信仰,它甚至過於龐大而令自己害怕相信。
這樣一來,理解便在矛盾面前分裂了。「不能顯現於世的東西」——一如《大鼻子情聖》中主角Cyrano de Bergerac消失在他代為書寫的情書之前——反倒因此裸露出來,而將主體推向一種處境:「我於我不在之處思」,因此有別於「我思故我在」。原先以為的「怎麼辦?」處境,卻在「猶豫不決」、「三心二意」之中給出了「可能性」的奧祕。它的偶然性所帶出揮霍無度的交纏,成為「永恆持續的一種折磨的狹隘形象」。用這種雙輸的方式來獲得雙贏,「每個人都是以反轉的形式接受訊息」,一如凹透鏡前的那只花瓶或是李維史陀眼中的野蠻部落。
於是,「匱乏」具備必要性的部署:慾望總是透過他人的身上看見自身的匱乏。如此害怕曝露,這般脆弱與孤獨。於是我說,我「是玻璃做的,透明而空虛,蒼白而脆弱。」然而那一個孤絕失落恐懼害怕的我才是最接近真實的自己。用這種角度回想傳統人類學的古典方法論:這種孤立也曾讓人類學感到恐懼,害怕自己僵化而變成石頭,或者乾脆以這種梅杜莎技法將研究客體變成石頭。
這種連恩式(R. D. Laing)自我分裂操作(或者按佛洛伊德的術語:痛苦經濟學),無望又卑微地處理自身一波接著一波的焦慮。一切複雜的思維是如此沈重而易碎:若是過於小心,深怕別人識破自己的存在;若是放棄謹慎維護,卻又讓自己直接落入絕望的深淵裡。這是一種處在幽微陰影下的自我包裝術,一如我們都曾經這麼認為:「自己是難以為外人所捉摸、看清透澈,或是拒絕為外人所賦予的標簽或理解。」正因為如此,我們學會避免瞭解對方而變得更不誠實;我們彷彿共同瞭解,「看清評價」成為一種變相的鄙視。於是我們又刻意表現自己是如此輕易識穿,因此反向小心呵護包裝的虛偽性。這麼一來,我們終究僅只於瞭解對方的表象,而避免想像中因為誤解而盤據在眼框周圍尚未掉落的眼淚。
如果「書寫是一種虛榮」(布賀東如此說),那麼這本著作既是瞭解也是矯飾。充其量,我們都只是一位聽故事的人。我將這本著作獻給我的學士論文指導教授余德慧先生,這一切的偽裝他都沒有戳破。
5 則留言:
怎麼辦~好怕買不到啊!
別怕。我會寄給你20本幫我賣。你賣了兩年之後,煩惱的應該會是:「怎麼辦?半本都賣不出去啊!」
這本嗎?我立馬上網訂購
http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CN10827012
我煩惱的是,到時候人手一本,在路邊叫賣還被回嗆:「早就看完了!」,這該如何是好?
應該是「圖書館隨便借都有,何必買?傻子。」
張貼留言